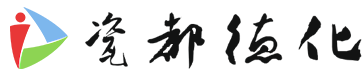◎ 西风
沉寂一年的扇子又被主人从角落里“请”了出来,然后用湿抹布擦得干干净净,置放在床头、案几或比较显眼的地方,以备不时之需。
冷清的扇子又重新派上了用场,不论如何,身边有了扇子,宛若缕缕清风犹在身畔,当暑热难耐时,便可顺手抓过,漫不经心地摇着,一股宜人的凉意扑面而来。你应该用欣喜和感激的目光望着那把扇子,当它在你手中摇曳生姿时,似乎有了不可言传的灵气。在夏天,人与扇子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与和谐,让我们在滚滚热浪面前,多了一些曼妙的诗意。
我喜欢捉摸问题,当然说出来也并不可笑:发明扇子的古人一定受到了什么启发,是摇曳生姿的树叶,还是展翅高翔的飞鸟?当我的答案敲定为飞鸟时,我就联想起仿生学和发明飞机的那位伟大发明家。当然,扇子只能流传于民间,它不可能像飞机那样登上大雅之堂。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答案,是因为有迹可循,苏东坡诗中的“羽扇纶巾”“烈日炎炎似火烧,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我想古人应该是受到了鸟儿舒展翅膀的启发,由此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把扇子。我国古时的羽扇,说不定就是扇子的始祖。只不过用羽毛扎成的扇子,好看不好用,多用于舞台上的古装戏。后来就有了香扇、折叠扇、芭蕉扇种种。
谈及香扇,我估计是古代大户人家小姐的心爱之物,工艺精巧美观不说,扇面上还有图案或文字,透着一股子文雅的书香气息。以扇传情,扇而且香,自是有了些俗媚的胭脂之气,但还是很有诗情画意。在经典的白话小说中,香扇出现的频率似乎并不比罗帕少,甚至有小说就以扇子定名,比如《桃花扇》。在这些行若流水的文字中,美丽贤淑的小姐持一把香扇,轻摇慢摇,自可摇出万般风情;倘若失态或羞涩,那香扇成了一道屏障,遮住整张桃花脸,或半遮半掩,便可起到掩饰作用。
我并不晓得扇子始于哪朝哪代何年何月,我感兴趣的是扇子的实用和诗意。谈到扇子,不能不提到济公,如今的一些折叠扇的扇骨上,依旧题着“济公扇凉风,好风此扇中”,可见济公把扇子的韵致和情调发挥得淋漓尽致,一把扇子持在他的手中,便有了洒脱与灵气!而在皇帝大巨手中,扇子便成了一种威仪和权力的象征,令人感到压抑与窒息。估计古时社会的底层人民,消受扇子带来凉风的概率甚少,比如农人,他们劳作在烈日烘烤的田野上,揩干脸上的汗水,又埋头眼前的农事。纵使腰里真的插着一把扇子,他们也不会有这份闲情逸致。
儿时家贫,手里不可能有一把称心如意的扇子。记得那个难耐的盛暑时节,姐姐不知从哪讨来一把半新不旧的折叠扇,我们姐弟五个抢着用,摇着摇着,那把扇子就散了架,着实让我们心疼了好一阵子。后来母亲编织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小席子,周围用布条缝严,再用个木条做扇骨,一把扇子就成了。尽管是四方形的略显丑陋的扇子,但扇起来依旧呼呼生风,煞是凉快。重要的是人手一把,我们再也无须争抢。
如今,扇子似乎有些落伍,它的作用大不如前,伴随电风扇和空调的出现,扇子生存的空间似乎愈来愈小,但因它的轻巧,翩翩的踪迹依旧可见。年迈的老者,喜欢用结实耐用的芭蕉扇,不紧不慢地扇着凉风,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,很是惬意。扇子应该不会绝迹,就像这个如火如荼的夏天,我还是时不时摇摇扇子,体验别样的闲情逸致,浮想一些深深浅浅的怀旧情结。